资管新规下的第三方财富机构(下):2008~2018年,十年兴衰启示录
从卖一单100万的信托产品纯赚2万,到2014年监管层明令禁止信托公司委托非金融机构推介信托计划,2008年~2018年,第三方财富机构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及转变?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李蕾

每经记者 李蕾 每经编辑 肖鴻月
“第三方已死?”——几乎每隔几年,市场上便会出现一次这样的声音。最近一次的起因是,2017年底资管新规的发布,又有业内人士喊出了,“那些靠信托刚兑起家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要完了?”
吊诡的是,在一片不被看好的声音中,这个行业的规模却一直在屡创新高——一些业内领先的机构已经将业务领域从原有的固收产品销售,拓展到了股权投资、房地产运营甚至不良资产处置。
所以你看,第三方不但没有死,反而在不断攻城略地、扩大自己的版图。
不过话说回来,和十年前成立之初相比,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不管商业模式还是业务逻辑,都已经发生了釜底抽薪的变化。那些没有转型、或许也无法转型的机构,也是真的无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十年兴衰史,是整个大资管行业发展的缩影,也为后者加上了一个不失精彩、无法磨灭的注脚。
2008~2013年:野蛮生长的1.0时代
国内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是怎样出现的?
西南财经大学ICFS财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潘席龙对于第三方机构有着多年研究经验。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过去普通投资者的理财主要都是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机构在做,“国内的金融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老百姓的理财需求却是综合的,单一的银行或者保险做不了这种工作。这个时候,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出现就很有必要性了。”
但若是要说这些机构的崛起,信托刚兑与银行飞单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07年的信托“新两规”,它使得信托计划作为具有放贷功能的直接融资工具,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迅速成为继银行之后总资产规模排名第二的金融机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无疑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享受了信托行业高速发展的红利。
一位沪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早期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商业模式非常单一:直接把信托公司的产品拿过来,借助银行等渠道、采取给客户经理返佣的形式进行销售,自己则从中抽取点差。
另一家大型股份制银行资管人士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作为一名银行客户经理,卖出一单100万元的信托产品,佣金不过就几千元;而如果是通过第三方,销售提成可以给到2%,还是税后,那么卖一单就纯赚2万元。“银行飞单就是这么来的。”他苦笑起来。
能给到银行客户经理这么高的返佣,那么这些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自己能赚多少呢?一位中型信托公司人士透露,依据标的产品资质的优劣,这些机构可以抽取1.5%~3.0%的佣金。掐指一算,一个年销售十几亿规模产品的小型第三方,每年就有可能获得千万级的收益。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充足的信托产品供应、庞大的市场理财需求,提供了巨量成长空间,短短几年时间里,第一批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便在这种野蛮生长的氛围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还能被称为“第三方”吗?在潘席龙看来,它们已经变成了“第二方”。
“按照国外的标准,第三方理财是专业、中立的机构,更多靠咨询、提供理财方案来盈利。现在国内的第三方机构,自己又当球员又要裁判,还要做评论员,这就已经有问题了。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果当初做得不规范,那么风险最终也会回到自己身上,这不能怪监管,要反思自己的原因。”
2013~2015年:初见成效的2.0时代
从2013年开始,监管层对于信托行业的政策开始收紧,于2014年、2016年相继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聚焦信托业风险,而且逐步涉入到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
更为当头一棒的是,2014年5月,银监会向各银监局及直属信托公司下发《关于99号文的执行细则》,明令禁止信托公司委托非金融机构推介信托计划,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原有的模式似乎难以为继。正如上述负责人所说,“大家都急了,开始找新业务做”。
那做什么好呢?
2012年底,第一家基金子公司成立;同一时期,私募基金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些机构的兴起,使得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产品结构开始分化——一些嗅觉灵敏的开始布局相关产品、抢占先机;不过对于更多的机构来说,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虽然一个新的时代,例如私募基金时代的来临,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但不少第三方机构,尤其是过去主要以信托产品为主的,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希望在原有模式下维系。随着监管趋严,很多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没有牌照、从业人员也没有专业资质,基金子公司和私募基金哪敢跟它们合作,都找银行、券商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第三方面临‘断粮’风险,还有一些就直接随着信托产品的萎缩和直销力量的崛起被淘汰了。对于一成立就顺风顺水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来说,这段时间确实挺难熬的。”回忆起这段历史,上述负责人不禁感慨。

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事实上,业内也不乏较早看到这类隐患、顺利转身的公司。
诺亚财富创始投资人、执行董事章嘉玉就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对于不再销售信托产品,“第一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趋势,国家政策要消除影子银行和刚性兑付也已经好几年了;其次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不可持续,更加期待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
不仅如此,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第三方高管坦言,刚性兑付“一定程度上是在喂养投资者的贪婪”。潘席龙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表示,长期以来,国内的国有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把投资人惯坏了,“觉得投资国有机构肯定没问题,没有风险意识”。而这些问题,都亟需打破刚兑才能解决。
不过面对监管的收紧,大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最初的反应都是“无所适从”,整个2.0时代充斥了太多焦虑却又茫然的面孔。
2015年至今:开启蜕变的3.0时代
虽然资管新规是2017年底推出的,但其实严监管的趋势从2015年便已初见端倪。在全新的3.0时代,整个财富管理行业都在尝试将商业模式升级——有的机构选择留在原地,继续做大原有的类固收产品销售;有的开始向行业上游拓展;还有的则收购资产管理牌照,或组建资产管理公司。
普益标准研究员陈新春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表示,在整个大环境转换背景下,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也需要转型。从业务格局看,有些机构可能会回归财富管理行业的本源,即做好对客户的理财规划,并进一步向高净值客户倾斜资源,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产品研究、投研团队建设等。有些机构可能转型为资产管理机构,直接代客理财、代客投资,并由债权型投资转向债权型和股权型并重的业务模式。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以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为例。章嘉玉介绍,目前其主要业务构成共分四部分:一级市场股权投资、二级市场投资、房地产板块(已从早期简单债权类产品向运营相关转型)、包括消费链金融和供应链金融在内的类固收产品。除此之外,其在2017年也成立了特殊资产管理部,专门做不良资产处置产品。
恒天财富总裁崔同跃也向记者提及,2016年至今,资管政策层出不穷,“在合规发展的指导思想下,不断拓宽产品线,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延续原有固收产品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权益类项目,股权投资更是我们2017年的重点布局。2018年,会进一步加强买方研究团队的建设,包括固定收益、权益、混合以及商品策略的研究,同时还包括资管行业的研究特别是二级市场的投资研究。”
一方面是大型第三方财富机构积极拓展新业务、谋求转型;另一方面则是小规模机构的专业化倾向。上述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负责人就表示,其公司近年已经开始向股权投资转向,“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章嘉玉对此表示,过去第三方财富市场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很多机构只是简单销售信托或债权类产品,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核心能力的建设至关重要”。
“2018年、2019年对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都是严酷的挑战,过去的模式必然会被打破。从业者首先要搞清楚: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要在哪个版块做?我认为这是2018年对这个行业最重要的问题。”
潘席龙也坦言,在当前的形势下,第三方理财机构该收缩的或许要适当收缩,回归主业、回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上来。“收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好好地练内功。这个市场空间还很大,不妨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为未来做好准备。”
 每经头条
每经头条
 每经热评
每经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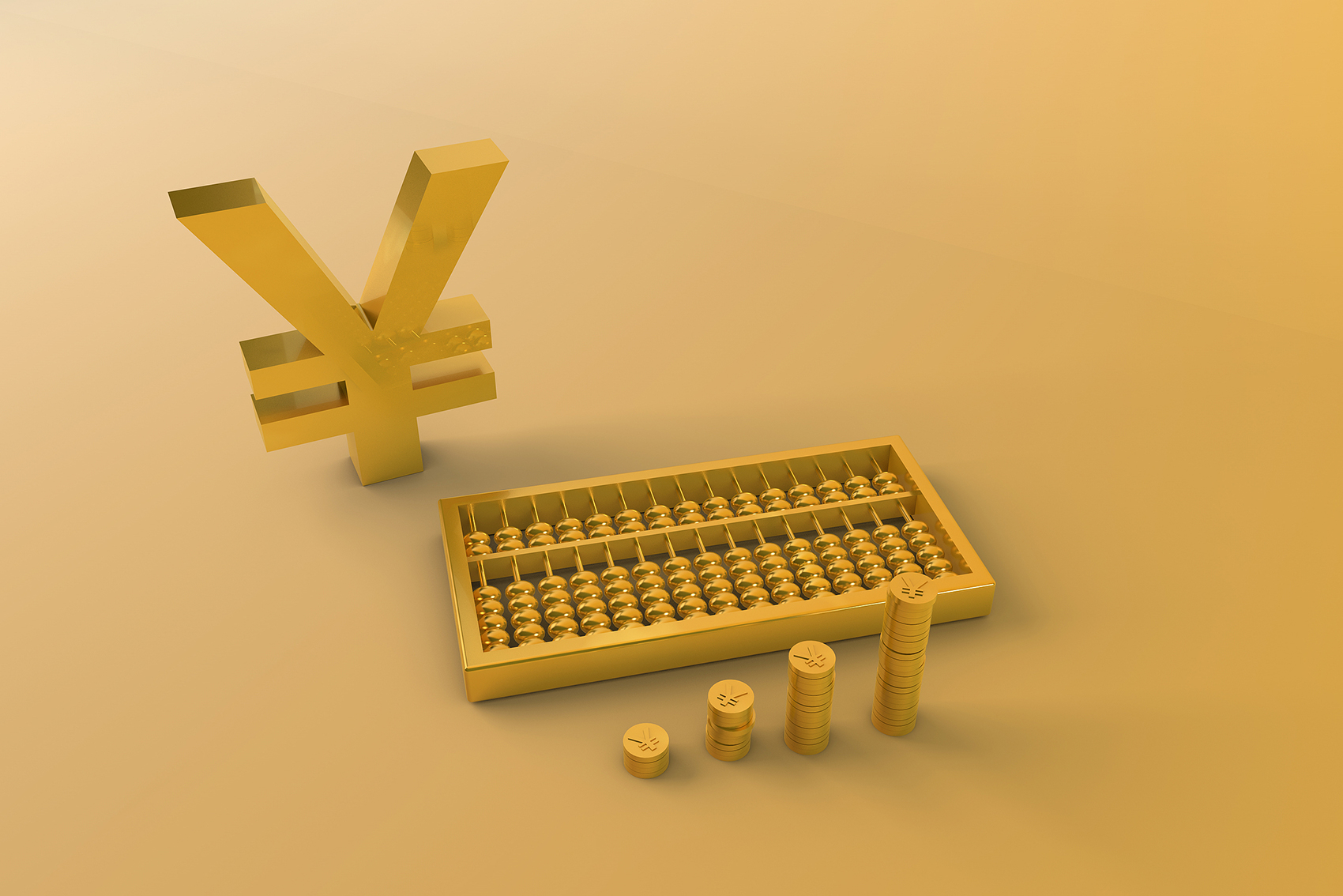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