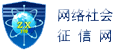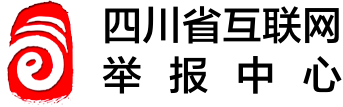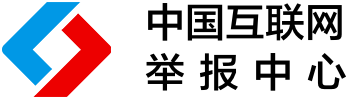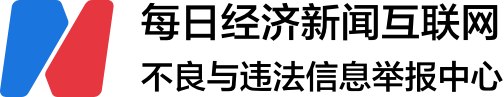我的乡愁与悲欢离合
火车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很多相逢的喜悦在这里发生,很多分离的悲伤也在这里发生。譬如,我三岁的女儿就和她姑姑家的小姐姐小哥哥在此上演了一场悲欢离合。
◎孙卫涛
火车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很多相逢的喜悦在这里发生,很多分离的悲伤也在这里发生。譬如,我三岁的女儿就和她姑姑家的小姐姐小哥哥在此上演了一场悲欢离合。
在初五返程的路上,人小鬼大的女儿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和哥哥姐姐一块儿玩了,于是就时不时用稚嫩的口气央求说:“妈妈,我不回北京。爸爸,我不回北京。”于是我们一直哄着说不回。可是,在检票口说再见的时候,女儿彻底爆发了,怎么哄也不行。
而就在年前的腊月二十八,他们三个刚刚在同一个车站经历了相逢的喜悦,手拉着手一块回老家过新年。
这不由使我想起在农村的快乐童年。我的家乡是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南和县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人世代为农,经济相对而言并不发达。在我的记忆中,人们平时的主食主要是玉米面以及很少的白面,一年到头见到不到几次荤腥。所以过年就成了小孩子最盼望的事情,因为只有那时候才能吃上鸡鸭鱼肉,才能吃够芝麻酥糖,才能和小伙伴一起放鞭炮,才能挣到一笔不菲的压岁钱,以及长长的假期。
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母亲做的“司糕”(方言)。那是用家里的黍子面做的,和成面团后在白面缸里放上一段时间。然后在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揉成长条切成圆块,放在油锅里炸一下。这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都围着火炉,趁着热乎劲儿吃上一口,觉得幸福得不得了。现在老家都快20年没有种植黍子了,更不要提“司糕”了。
然而家乡于我而言并不总是欢乐的记忆。这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父亲和大爷(父亲的哥哥)一起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市里干点建筑方面的苦力挣钱养家,直到后来承包了一个大工程赚了不少钱。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大爷突然掌握住了所有的钱,对我父亲说没有一分钱。于是,吵架、打架、打官司在此后的几年不断上演,甚至还有人在我们家里下毒。
这件事让年幼的我早早尝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因为我大爷掌握住了钱,所以村子里的人很多都向着他说话,甚至父亲这边所有的亲戚都和我们断绝了来往。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时不时受到一些外人的冷嘲热讽。父亲抑郁成疾,患上了轻度脑梗。
家里的经济一下子紧张起来,那时候我一直想辍学去学一门汽修技术好赶紧找个工作养家,可是被父母劝住了,我知道那是父母希望我能为家里争口气。还记得去上大学前的那个晚上,母亲一次次进到我的房间,一会整理这个一会整理那个。其实该准备的东西早已经准备好了,我知道母亲有很多话说,但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她终究还是不知该如何表达。
2009年,我刚刚参加工作一年,也结了婚,本以为可以好好孝敬父母的时候,父亲却突然被诊断出了胃癌晚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去世了。最后的几个月,本来150多斤的父亲瘦成了不到100斤。
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在兄弟姐妹里边,父亲待我最亲,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总是在别人面前夸我,以我为荣。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去串门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每次都是背着我走在夜深人静的小巷中。父亲体谅我的难处,偷偷对母亲说:“要是咱没钱就不治了,别让孩子为难。”听完后,我顿时泪流满面。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清明节,我因为有事没有回家祭拜。但是那几天我总是不舒服,神情恍惚。我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笑着说,那是你爹去看你哩。我心里顿觉愧疚。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并没有守在身边。母亲告诉我父亲最后还是惦记我:涛儿怎么还不回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那一刻我真的祈求有神明的存在,让我再看看父亲,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在梦里见上一面,和我说说话。可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梦见父亲一次。
直到女儿出生,我才突然意识到,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传承,老的生命逝去,新的生命诞生,一代代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轨迹就如同一趟奔向死亡的列车,我们都知道终点,但是不知道火车行走的路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车开车,不知道谁上车谁下车。
如今的乡愁于我而言,就是逢年过节带着女儿回家看看母亲,祭拜一下父亲。我不知道等母亲不在的时候,我还会不会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
曾有几次出差,不少司机一开口就问,你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竟一时语塞。我是来自北京,但我的故乡在河北的那个农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回不去我的故乡了。
 每经头条
每经头条
 每经热评
每经热评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