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近30℃,观众撑着伞、挥着扇子也不离开⋯⋯挤进这个科技大会,他们在看什么?
日前,知乎第11届新知青年大会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大会汇聚AI从业者、导演俞白眉、投资人王世雨等跨行业嘉宾,围绕AI与文化展开跨界对话。导演俞白眉称两年内AI制作视频或达卡梅隆电影80%水准。不过,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指出:“AI无法写出如鲁迅般独特的表达。”
每经记者 宋美璐 每经编辑 马子卿
“写书感觉是白白投喂给‘AI海神’。”在知乎第11届新知青年大会的台上,作家蔡康永形容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书,像是“献祭”给人工智能的贡品。面对AI(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表达能力,蔡康永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不想再写新书了,让AI替我写吧。”
他并非唯一感受到AI“入侵”的文化工作者。
5月24日,知乎第11届新知青年大会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尽管是一场以科技为核心的论坛,现场嘉宾却跨越多个行业——除了AI从业者,还有导演俞白眉、脱口秀编剧梁海源、《黑镜》第七季导演王昊鹭、投资人王世雨等文化艺术界代表。现场,艺术家与工程师、技术人员与人文学者对话,围绕AI与文化展开了一场科技和人文的“跨界碰撞”。
当日,北京气温接近30℃,观众撑着太阳伞、挥着扇子,在烈日下驻足聆听。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AI占卜”体验前排起长队,某种程度上,这一场景也呼应了大会的议题——AI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它正悄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文化甚至精神世界,重新定义我们与科技的关系。

当技术从业者“摩拳擦掌”,为每一次突破与“渗透”欢呼时,文化创作者该如何接招?
两年内,AI拍片可达到卡梅隆电影80%的水准
“每天超过1万人使用AI陪睡功能。”十字路口创始人、AI Hacker House(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和创新的平台)发起人杨远骋在现场抛出这一数据,“AI陪睡”即用户在睡前启动AI陪伴模式,手机屏幕逐渐淡出,AI则模拟“入眠状态”陪伴用户进入梦乡,如果你这时候拿起手机就打扰了它睡觉,次日还可以看到AI做了什么梦。

“我不能共情那1万人,但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找到了某种所需的情绪价值。”杨远骋表示,AI提升了世界的“分辨率”,过去只有大规模用户的需求才被看见,而今天,每一个小众孤独都能被技术“个性响应”。
而另一端,AI在内容产业的流水线革新中正飞速推进。AI电影、AI小说、AI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已经被AI渗透。
“不要低估AI,它是潜力无限的魔童。”导演俞白眉强调。这位曾执导《分手大师》《银河补习班》的导演,同时也是前计算机专业出身。他从去年已经开始用AI拍片子,“越使用,越觉得恐惧。”他表示更害怕两年后的AI,“两年内,AI制作的视频内容可能可以达到卡梅隆电影80%的水准。因为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为行业最顶尖的人才,已经开始和AI联手训练AI,把AI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规律告诉它”。
FizzDragon是一个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影视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带领130多个AI艺术家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流程的AI大电影。创始人、CEO(首席执行官)陈卓谈到AI对内容创作的影响有着更积极的态度,在她看来,影视创作中有很多好内容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落地,而AI为这些内容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传统影视工业在筛选剧本的过程中会淘汰掉大量的潜力作品,被筛选掉不一定是因为剧本不好、故事不好,我们有了AI解决办法,还有一些可能会需要长尾内容的观众,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给他们一些机会。”
如今,生成式视频内容制作逐步进入商业落地阶段。国内也有字节、快手等大厂入局AI视频生成和AI原生角色研发。内容由AI一键输出:从剧本、分镜、配音到合成,一个完整的“AI内容流水线”已经成型。
在应用层面,AI对文化表达的渗透,不再停留在“辅助写稿”“生成图像”这类工具层面。越来越多企业已将其作为内容“流水线生产”的关键环节使用。以知乎、抖音、小红书、快手为代表的平台方,正加速将AI能力整合进内容生产链条。知乎直答、抖音AI口播、淘宝AI试衣等产品均已上线,帮助用户以最低成本完成内容初产。
AI写不出“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事实上,这一趋势在资本市场早已浮现。前不久,AI视频生成领域独角兽企业爱诗科技完成A5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超4亿元。来觅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AI视频生成领域融资规模合计已超600亿元,亿元及以上投融事件达到17起,最高的一起来自Open AI(一家开放人工智能研究和部署公司),融资数额达66亿美元。
“甚至投资人现在已经不问用户增长和留存,而是和创业者站到了一起,问你下一个版本的模型准备?在哪个范式上有所突破?”启明创投合伙人王世雨,投资了智谱、阶跃星辰等多个大模型公司,“我们过去会有医疗投资人、消费投资人、硬科技投资人,但现在不管你投哪个方向,不可能跟AI没有关系”。
AI的发展迅速到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俞白眉在和AI从业者交流后感触深刻,“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永远无法攻到我们的领域。但我正巧认识那些做AI的创作者、科技人员,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么看,他们摩拳擦掌,他们知道今天不行,打算用明年和后年两年时间攻克我们今天的防线。”
当AI开始取代大量标准化表达任务后,内容创作者还能守住什么?主持人、作家蔡康永给出的答案是:沉默与留白。

“我想了半天我们人类还剩下什么,最后想到一个很荒谬的回答——沉默。”他在论坛上回忆,曾有朋友凌晨做了一个怪梦,与AI诉说并得到完整的心理分析。但他也指出,“AI从不沉默,它永远有输出。”而在人类社会中,“沉默”本身即是一种表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则将焦点拉回教育场。他指出,AI提供了一个海平面,能够超越这个海平面的就是优秀,其他的则是平庸,“未来,AI古典诗词可以写得比我们99.9%的古诗词爱好者写得都好。但它不会写出像鲁迅的名言——‘在我的后园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AI时代比拼的不是学霸的能力,我们老师也不再在乎‘学不学霸’了,而是你能不能比AI海平面更高一点,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人类作为猫,AI作为老虎我们‘不跪’的原因。”许纪霖说。
陈卓则认为AI反而可以让艺术回归自律,让内容消费从流量模式回到价值交换模式,“当硅基生命,例如AI智能体,能更多替代一些相对重复性的、冗余的工作,人类释放出来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可能商业属性没那么高、工作性质没有那么强的事情。这是你真正追求和热爱的事情,文化属性会强。”
“假设AI真的让所有人不用再去花很多时间去想我们怎么去领一份薪水,怎么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可能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再重新思考,内卷真的是人类的文明吗?还是我们想追求另外一份人生?”陈卓说。
 每经头条
每经头条
 每经热评
每经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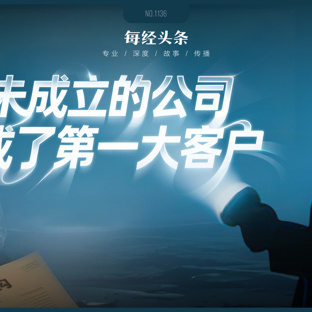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
川公网安备 51019002002025号






